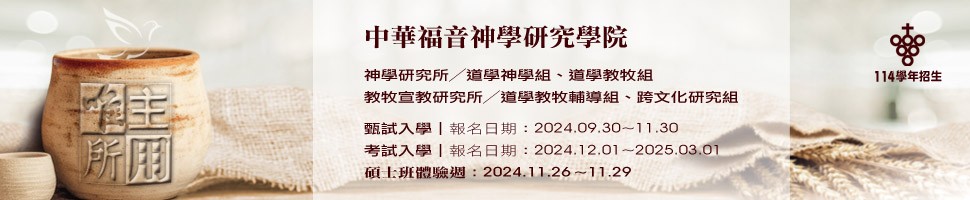◎徐硯美
曾經在網路上看過一幅連環的插圖,是一盆仙人掌放在一處,有一個人走過去,擁抱了它,走的時候,身上帶了幾根刺;然後又有一個人走過去,擁抱了它,走的時候,也帶了幾根刺。
漸漸地,在經過許多人的擁抱之後,這盆仙人掌,變成了一個人,他給了最後一個抱他的人,深深的擁抱。
我們用甚麼來改變人?
基督徒非常喜歡「見證」,不管是自己分享,或者是聽到別人分享,通常,大家在講見證的時候,都會很像我們看過的那些日本改造房屋節目,有一個「Before(改造前)」然後有一個「After(改造後)」。
節目過程,就會拍攝一位專業的室內設計師、建築師,如何看見原來屋主有的問題,然後提出一連串的解決方案,設計、施工;最終整個節目最吸引人的,莫過於原屋主看見新家的那一刻。所以,我們就是那間房子,同時也是那個原屋主,而前來改造我們的,就是上帝。
可是,往往我們欣喜地做這樣的見證時,卻忘記了好幾個重要的問題:不是我們改變成甚麼樣子,而是為什麼上帝有能力可以改變我們?而這個能力究竟是甚麼?我也能夠有這樣的能力嗎?我要怎麼效法基督,也能夠成為帶來改變的人?
城市孤島中最孤獨的照顧者
《瀑布》是由金獎導演鍾孟宏繼《陽光普照》之後執導的第五部劇情長片,此次也入圍了今年金馬獎十一項大獎。電影的背景貼近時事,劇中女兒小靜(王淨 飾)所就讀的高中有人染疫確診,需要居家隔離;而母親品文也因為公司知道此事,隨即要求她回家,二人便展開了十數天的「近距離」相處。
十七歲的小靜正值青春期,有許多言行比較反叛,品文也對她較為嚴厲,所以,電影開始不久,就可以感覺得到母女之間的張力逐漸升高。但是,這份張力並不單純,因為品文所認知的小靜,隨著敘事視角的轉移,觀眾就會逐漸發現,品文所認知與感知到的現實與事實有很大的出入,從女兒小靜的視角發現,品文生病了。
不同近年來以精神疾病為議題的電影作品,《瀑布》在切入品文的身心狀態異常時,並不強調「病因」,所以,導演並非把焦點放在「問題」與「解決問題」上。對我而言,他更加寫實地掌握了,絕大多數像這樣情況在現實發生時,身邊最親近的人首當其衝,他們得重新適應一個既熟悉,又陌生的「親人」。
這對母女用「相依為命」來形容並不妥切,反而,我更會用「孤島」這兩個字,形容她們就身處在這座看似文明、繁忙的城市之中,從周圍的鄰居,樓下的管理員,再到品文公司一同工作十數年的同事、上司,看似寒暄與關心的日常,在這家人發生變故之後,也變得冷淡甚至是排斥。
小靜的父親早已與品文離婚,另組家庭。在整部電影當中,他短暫的出現又離去,每一次,都只是顯示出他對現況的無能為力;於是,母女兩人好像一個在白襯衫上的墨水印,在如常運作的大城市裡,成為了眾人不想看見的「黑點」。整個大環境,讓小靜這個還在準備升大學考試的十七歲少女,成為了這個孤島中,唯一且最孤立無援的照顧者。
與疾病共存的力量
電影中,小靜面對到品文的歇斯底里、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靜、惡意的言語,承受了極大的壓力;可是她並不停止陪伴,甚至,不輕易將凝視生病母親的眼睛,從那些最不堪的生命樣貌中轉移。經常聽見她在整部電影中,深吸一口氣,輕喚著「媽媽、媽媽」;這一次又一次的「不轉身」,成為整部電影中,既痛苦殘酷,卻又溫柔堅毅的力量。
在劇情的發展中,品文的病情似乎並未有突飛猛進的好轉。我想原因就是,站在觀眾的角度,甚至是現實的角度來說,陪伴像品文這樣的病人,多想要一覺醒來,好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,疾病消失的無隱無蹤,一切如常,過往的日子又是陽光燦爛地出現在眼前。
可是,現實就是絕大多數的時候,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。我們都得像小靜一樣,面對一種未知,既不知道疾病甚麼時候會康復,更不知道在那些偶爾好轉的某些時候,又會怎麼急轉直下。

但是,電影中的品文卻在這樣的疾病中,如同拆解一顆、在心底一個串連一個的巨大炸彈那樣,一點一點地把過往的創傷、不願意面對的事實,慢慢清理。她從沒有病識感,到感受到自己的問題,到與疾病共處,有餘力時,用她僅存的精神,盡可能地回到社會當中繼續生活。
然而,之所以能夠如此,也是因為小靜先展開雙臂,擁抱了品文,即使那些刺在擁抱的過程中,也讓小靜受傷。但是,一次一次的擁抱過程裡,當刺全然被拿去,剩下的,就是最原始最脆弱的,卻也最寶貴的,真實之親。品文最後是否有好起來,留待觀眾去發覺,但這位母親卻在女兒與她共存的過程裡,找到了與病共存的勇氣與力量。
新造的人是被愛出來的
「若有人在基督裡,他就是新造的人,舊事已過,都變成新的了。」(哥林多後書五章17節)基督徒很喜歡用這段經文宣告,可是,卻鮮少去對應整段經文的脈絡,保羅在這段經文的前面,解釋了甚麼是「在基督裡」:「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,因我們想:一人既替眾人死,眾人就都死了; 並且他替眾人死,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,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。」(14-15節)
「在基督裡」的意思,是耶穌基督為我們死,而我們為他而活,所以,新造的人是怎麼來的?保羅告訴我們,是被長闊高深的愛,愛出來的。以致我們跟人相處的時候,會讓他感覺到「在基督裡」嗎?還是反而是越接觸我們,他們越被隔離「在基督外」呢?
我們都希望影響他人的生命,改變世界;但是回到《瀑布》這部電影,也回到開頭所說的那幅插圖,可以重新問問自己,我願意成為那個「抱刺的人」嗎?甚至最終,他擁抱的未必是我,但我願意為了他有一天能再擁抱他人,而帶走他的刺嗎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