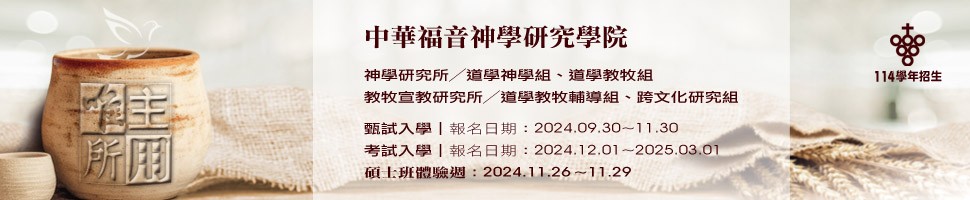【特約編譯趙亞設/報導】新冠肺炎(COVID-19)大流行已持續近兩年。當人們開始在談論後疫情時代的工作與生活規畫時,一個有史以來變異最多、可能使得所有疫苗失效的變種病毒Omicron卻突然來襲,迫使各國的防疫措施改弦易轍。
疫情使許多基督徒的愛心冷了,《Relevant》雜誌資深編輯泰勒.赫卡比(Tyler Huckabee)撰文提醒基督徒做好防疫,在疫情期間為主得人。他的分享如下:
新約聖經記載耶穌共行了37個神蹟,其中27個與醫病有關。福音書有時記錄詳盡,例如馬太福音記載癱子的四位朋友從屋頂放癱子到耶穌跟前。但有時只記載耶穌「治好了許多害各樣病的人」(參馬可福音一章34節),或說凡摸著耶穌衣裳繸子的人都醫好了(參馬可福音六章56節)。
約翰福音廿章30節雖指「耶穌另外行了許多神蹟,只是沒記在書上。」但是大部分神蹟與醫病有關。沒錯,耶穌可以行在水面上,將水變為酒,還有好幾次幫助朋友得魚。不過耶穌行神蹟的名聲,主要建立於醫好病人上。其實耶穌不一定要醫病,咒詛仇敵受苦也是輕而易舉。不過耶穌希望讓人知道,祂會醫病。
基督徒因不顧安危照顧病患揚名
緊隨耶穌,初代教會使徒保羅、彼得同樣會行神蹟,例如醫好瘸腿的乞丐。但行神蹟並非早期教會醫療事工的唯一途徑。路加福音及使徒行傳的作者路加,也是一名醫生。那時候,病人遭社會遺棄,但教會照顧、關懷病人,並因此取得了名聲。

耶穌和門徒會走進痲瘋病人群體,與被隔離的病人聊天。埃及亞歷山大城主教迪奧西尼(Pope Dionysius of Alexandria)在他殘存的書信中,也記錄了二百年後的基督徒,在做同樣的事。「很多人滿懷弟兄的仁慈和愛心,不顧自己安危,探訪病人。」
在二世紀可怕的安東尼大瘟疫(Antonine Plague)爆發期間尤其如此。這場瘟疫殺害了羅馬帝國四分一的人口。有歷史學家認為,它對基督教早期的興起有所助益。因為在瘟疫襲擊時,非基督徒紛紛棄罹病的同伴於不顧,只有基督徒留下來幫助他們。
後來的賽普勒斯大瘟疫(Plague of Cyprian,發生於西元249-270年間,又稱居普良大瘟疫)對基督教也產生了類似的影響。迦太基教會主教居普良(Cyprian, 約200年-258年)見證並描述了這場瘟疫,他教導基督徒少花時間哀悼死去的人,多花些時間去照顧受苦的人。基督徒以照顧所有人而為人所知;正如教宗彭謙(Pontianus)補充:「照顧人不是只照顧主內弟兄姊妹。」
古羅馬時期沒有所謂的醫院,大部分醫生自學成才,普遍受到質疑,最佳的醫護往往留給負擔得起的人。西元325年的尼西亞公會議(Council of Nicea),為遵行彼得前書四章9節的教導,決定開設療養院,收納病人和窮人。教會希望每座大教堂都附設臨終安養院。
君士坦丁堡的聖沙默遜(St. Samson)醫院及現代土耳其的巴茲爾(Basil)醫院就是最早期的兩個典範。約西元390年,一名富有的基督徒寡婦指名要聖傑羅姆(St. Jerome)在西歐開辦第一所醫院。到了12世紀,君士坦丁堡已有兩間設備完善的醫院,員工有男有女,包括各科專屬病房。

馬丁路德:基督徒需善盡防疫責任
隨後黑死病橫掃歐洲,造成7,500萬人死亡。西元1525年,蔓延至威登堡(Wittenberg),馬丁路德寫信提醒基督徒在疫情期間要善盡防疫責任;屬靈上要勤奮禱告,實務上要保持警覺(保持社交距離和服藥)。他寫道:「我祈求上帝憐憫,保護我們。因此我應該要做好環境消毒、維持新鮮空氣、管理好藥物並在有必要時服用。我應該避免去一些我不需要去的地方,見一些我不需要見的人;以避免受到感染,以及因我的疏忽,讓自己染疫或傳染他人致死。這才是敬畏上帝的信仰,不傲慢、不莽撞,也不試探上帝。」
十八世紀時爆發克里米亞戰爭(Crimean War),南丁格爾(Florence Nightingale)革新護理師工作,不眠不休地改革軍醫院的條件。在她的領導下,為貧民甚至黑社會罪犯,成立醫療機構。她常說自己十幾歳的時候,受上帝呼召,終身服事病人。她放棄家人所提供的上流社會生活,無視因她美貌而被吸引的富家公子,每天工作20時,不斷進行研究,落實護理工作。

其他基督徒在醫護行業的慈惠事工也多不勝數,從宣教士傳福音時加入救護知識,到天主教的非凡傳承—─護士服便是從修女服飾沿襲而來。
其他基督徒在醫護行業的慈惠事工也多不勝數,從宣教士傳福音時加入救護知識,到天主教的非凡傳承—─護士服便是從修女服飾沿襲而來。今日基督徒似乎對捍衛自身權益更感興趣,但歷史上有更多基督徒放棄自身權益,服務他人,似乎也更符合聖經教導。
我們既不是耶穌,也不能靠衣裳繸子醫治病人,但我們可以順服祂的呼召,參與耶穌一向為人所知的關顧病人的工作。(資料來源:Relevant Magazine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