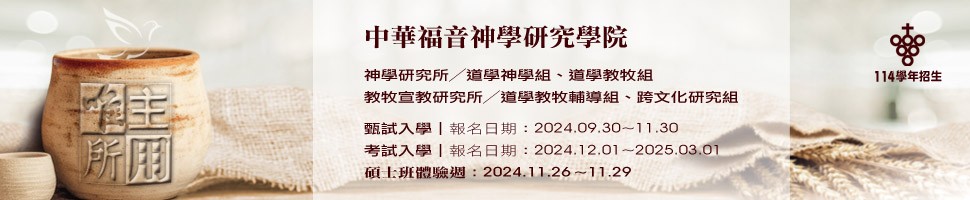◎徐硯美
已故的管理學大師彼得.杜拉克曾撰寫過一本小說《行善的誘惑》,講述一個天主教大學校長,因為不續聘一位化學系教師,引來了該名教師妻子對其發動黑函攻擊。
起初校長面對所有謠言,都以自己恪守的職場倫理與原則安然度過,身邊的人也為其捍衛名譽;可是,隨著時間越久,眼見風波不止,這位校長的信心也隨之動搖了,甚至覺得倘若自己動用職權,為該名教師在別的學校另謀職位,也就平息這場風波。
但他沒有想到,這一舉動,不僅將自己先前所做的一切全都付諸東流,更引來外界臆測他是否就是個濫權的慣犯。這個在他看似「善行」的舉措,也看似顧全大局,讓大家都能夠獲得雙贏,到底為什麼會為這個校長的名譽帶來如此大的衝擊?
小心十字路口的禱告
在聖經馬太福音第六章,耶穌對門徒說:「你們要小心,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,故意叫他們看見,若是這樣,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。所以,你施捨的時候,不可在你前面吹號,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裡和街道上所行的,故意要得人的榮耀。我實在告訴你們,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。」(馬太福音六章1-2節)
我們不會說,在彼得.杜拉克小說中的那位校長是個「假冒為善」的人,但是,耶穌卻要我們非常小心注意自己行善的「動機」。
例如,那位校長有個比較正向的動機是:顧全大局,以和為貴;但是相對地,一個隱藏的、不那麼正確的動機是:息事寧人,保全自己與學校的面子,甚至是維護自己長期以來經營的教育成果。以致,在正確與維持表面秩序之間,他選擇了後者。
我們往往檢視自身動機的時候,都忘了一件事,就是每個人其實都是「自我說服」的高手,合理化自己的行為、否認指控,甚至轉移焦點把問題丟給他人,這些都會讓我們無法正視自己行為最深層、最真實的動機。

為寫作體驗清潔工作的作家
《失業風暴》是2021年改編自真人真事的法國電影,故事敘述一位知名作家瑪麗安溫克勒(由茱莉葉.畢諾許飾演),為了調查法國社會底層的生活樣態以及失業情形,隱瞞自己作家身分,前往法國北部一個港口城市卡昂居住,並且天天前往職業介紹所報到,最終,她謀得了一份清潔工的工作。
這個角色的原型,是位名叫芙蘿倫絲.歐貝納的記者兼作家,她在2010年寫下了《資深記者化身底層階級180天》這本極具爭議性的紀實報導文學,撼動了法國社會各個階層。
在故事裡,瑪麗安與其他人一同接受清潔工的訓練,她告訴其他人,自己是被老公惡意拋棄,不得不出來找工作。她深刻地融入一群女性清潔工的群體中,與她們一同在寒冷的清晨與深夜,往返公廁、集合住宅或者是渡輪,做著最粗重的活,領最低的薪資,睡最少的覺,連生病都顯得奢侈。

最難割捨的是真摯情感
瑪麗安與身邊這群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女性清潔工打成一片,相互扶持,甚至,有人看她沒有車子前往工作地點,就借了她一輛代步車;有著三個小孩的單親媽媽把她邀請回家,為她慶生。
這些真摯的情感都讓她對隱瞞身分一事感到不安,可是,每當她回到自己租屋處,一字一句把這些體驗敲打在電腦螢幕上,她知道這將會是一本重要的著作。

從瑪麗安的角度來說,她當然可以說自己這樣的隱瞞行為,是為了能夠更貼近社會底層,近距離觀察與記錄。可是,電影裡有個很重要的情節,當瑪麗安新書發表會後的晚上,此時的她已經離開了清潔工的工作,昔日在工作上最親密的友人找到了她,把她載至她們曾經清掃過無數次的渡輪旁,希望她再陪她們打掃最後一次,只需要一個半小時。
但是,此時穿得時尚又乾淨整潔的瑪麗安拒絕了。電影沒有明確交代她拒絕的理由,同時,我們也可以說,瑪麗安所做的事,寫一本書來揭露時弊,確實比陪她們一同打掃更能激起社會的關注。
這是個很好的思考與辯證議題,到底是引起社會關注,解決問題重要?還是,生命對生命的陪伴,人與人之間的真誠更重要?或許問題不該這麼一刀切,但是,面對這二者如同電影中陷入兩難時,我們會怎麼抉擇呢?

陪伴是一生的決定
陪伴可以不是時時刻刻,但卻是一生的決定,一旦我們真切地走入他人的生命之中,那代表的,是他人也將生命交付我們。
信任在這個時代的關係之中,是一個越來越稀缺的要素,人與人之間,往往建立在供需、利益,甚至建立在虛無之上;在關係中「做什麼」遠比「只為理解與靠近彼此而做」更加重要。
所以,人與人之間好像一旦沒有事情可做,一旦無聊,就覺得已經走到關係的終結。可是,我們能否不只是這樣呢?
我曾經參加許多短宣隊,去到一些偏鄉接觸到當地青少年,他們甚至是走了好久的路,揹著幾件衣服來參加的,一整天活動結束之後,就在活動場地打起地舖睡覺。
三天兩夜的營隊讓我們建立起相當真摯的情誼,可是,當我們要離開,其中有一個孩子突然很激動地抓著我的手說:「為什麼你們都是來一下下就走?為什麼你們的愛都只是一下下?」那時我的年紀也不大,這個問題讓我一下子語塞了。
《失業風暴》在談的,不僅僅是善意謊言的可行與不可行,更重要的是,它碰觸到許多人在面對「關懷」、「憐憫」、「給予」的過程中,非常隱晦與深層的動機——我們所做真的是出自於愛嗎?
還是,我們很有可能是在消弭看到這些事和人,在自己眼前發生的時候,那種罪咎感與無力感?
或者,我們透過這些給予的過程,也在重新找到自我價值;我們在自我認同與他人的認同之中,漸漸地享受行善,可是,這些接受我們行動的對象,他們除了在資源上被救助了,在內心上,他們真的感受到我們與他們在一起嗎?他們的喜樂有被我們同喜樂?他們的哀哭有被我們同哀哭嗎?
直到今天,我都會思考著那個孩子問我的問題,以致,我也想把這個問題透過這部電影,與讀者一起省思:愛,可不可以不只是一下下?